作者:张生珍
科幻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经常超越“人之常情”,然而科幻小说家在创作中实则流露出对人类在运用科技方面回归人之常情的渴望,因为科技本身并无伦理之争,其所带来的结果却值得创造者与使用者进行伦理的考量。科技伦理(Technoethics)这一词语由加拿大科学与技术哲学家罗奇·卢皮奇尼提出,强调科技发展的道德意义、科技使用的道德责任、科技应用的道德风险评估等伦理考量,其终极要义是保护并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在科幻小说中,技术的进步与人性似乎是难以交融的平行线,作者希冀可以找到一个交叉点来审视二者的矛盾冲突,故事的最终走向通常会回归到其本质问题:技术的进步最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
科技伦理意识的觉醒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科学技术自其诞生之初就逐渐与伦理关联在一起。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念将“知识”与“美德”并置,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宣言高度肯定了科学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技术推动伦理道德的发展,而伦理道德则相对独立,并反作用于科学技术。长久以来,科学技术都被视为一种正向的推动力量。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利用科学技术在人类身上所做的生物实验开始引发人们反思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二战结束前的原子弹爆炸事件更是拨动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价值反思的琴弦,点燃了科技伦理诞生的历史火焰。人与自然、科学与自然等的关系成为现代伦理学关注的重点,并引发人们不断追问,应如何规避和应对现代科技带来的巨大风险?
“人”与“非人”是否有界?
1818年,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就反思了科技伦理的问题。弗兰肯斯坦身上没有科学家应有的正义与理性,而是一个滥用科学技术的魔鬼。他随意创造生命,却未能赋予生命应有的尊严。他所创造的怪物被拒斥于人类社会之外,而弗兰肯斯坦本人最终也和他的所造之物一起沦为了科技的牺牲品。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与“非人”的关系,重新定位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著名科幻小说家丹尼尔·凯斯的星云奖获奖作品《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正是围绕“人”与“非人”的模糊边界而展开。书中主人公查理·戈登经历了从依靠手术实现智商提升,到珍视生活、实现心灵成长的过程。先进的手术技术让他体验到了变聪明的快感,却依然未能帮助他赢得应有的尊重。书中的研究人员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名,让查理成为提升智力手术的实验对象,却从未向查理解释清楚手术的目的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查理同实验室的小白鼠阿尔吉侬一样,只是任人摆布的“非人”存在,是为医生、教授等研究人员带来名利的工具。
手术后变聪明的查理开始对知识充满渴望,大量阅读莎士比亚、弥尔顿、牛顿、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以及所有其他名字,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在我脑海中回响”。查理想要通过对知识的占有彰显自己已然成为聪明人,但学习知识却让查理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不再相信权威,不断对权威的论断发出挑战,也自此陷入了社交障碍的状态中,人们拒绝与查理交流,甚至曾经治疗查理的医生与教授也不愿与查理再有往来。究其根源,人们惧怕的不仅仅是查理的改变,而是他们与查理之间关系的变化,害怕自己成为被查理管控的对象。在福柯看来,知识就是权力,拥有知识便获得权力。查理曾经的智障让他失去了拥有知识的能力,成为面包店打工人中的另类、医生和教授眼中的“他者”。然而,一旦查理获得知识,成为掌控话语权力的主体,人们便对其充满敌意。因此,查理变为聪明人的这一变化最终导致他失去了面包店的工作。
当智力增长后的查理获悉手术最终会失败,他将像实验老鼠阿尔吉侬一样退化回智障状态,甚至不得不面临死亡时,查理陷入恐慌,难以接受智障的自我。先进的科学技术未能使查理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反而分裂了查理的自我。查理否认术前自我和术后自我是一体的,而是让位于一种更碎片化的自我意识,拒绝接受他的智力残疾。
随着智力不断退化,查理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另一个智障的自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那是查理,而不是我。他脸上那呆滞而疑惑的表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仿佛只要我说一句话,他就会转身,跑进镜像世界的深处。但他没有跑。他只是回望着我,嘴巴张着,下巴松弛地垂着。”查理从智力上升、达到巅峰到回落原有状态的过程,也是他审视多个自我,并在此过程中开始认识和接受不同阶段自我的过程。在小说结尾,查理要去为残障人士开设的沃伦之家,但这也是他主动作出的选择。
科技伦理中的“人之常情”
如今,人与科技间的融合与依存愈发突显。若要实现人与技术间的可持续依存,需要在充分尊重创造之伦理和技术使用之伦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当代科幻小说家就曾批判科技应用中的人类利己主义。克隆人是仅次于赛博格的第二个最常被提及的后人类例证,赛博格被认为是人与机器的混合体,而克隆人是人类细胞的重建与组合,是纯粹的人工制品。尽管组建克隆体的物质是人类基因,但其人造属性使“它”成为有别于人类的非人类存在。但克隆人及克隆技术引发了人们的一系列伦理思考:克隆人是否应具有人的权利?克隆人应当被界定为何种身份?
2005年,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通过讲述克隆人的成长经历,试图阐释克隆人议题中的一个敏锐话题:人类造物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如何?石黑一雄并未开宗明义地指明小说中寄宿学校的学生为克隆人,而是以细节提示读者,这些孩子的身份为器官捐献者,其存在目的就是挽救衰萎的人类生命。然而,克隆人却并非没有思想、仅有人类生物性特征的个体。书中的克隆人在一次次的器官捐献中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在石黑一雄的悲凉笔调中,映射出对人类所作非人道行为的反思,以及对于科学创造尊重人性、拥有人道关怀、回归人之常情的渴望。
上述作家书写的故事均发生在地球之上,而在航空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当下,星际关系以及星际合作同样成为科幻作家的关注重点。当代科幻小说大师金·斯坦利·鲁宾逊的《2312》就将地球置于太阳系的背景中,强调在人类能够成功运用高科技将荒芜肃杀的行星转变为宜居星球的24世纪,即使时空转移、居住星球发生变化、人工智能高度发达、机器人与人类共存、科技已经发展到能够改造人体,人性关怀在任何时空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依然未改变。
“你们好,我叫斯婉,从水星来。”这是故事主人公遇见智能机器人时的自我介绍,也是作者鲁宾逊为读者描画的300年后人类生活的缩影。书中来自太阳系不同星球、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之“人类”,与以酷立方机器人为首的高度集成的量子计算机之“非人”共存。酷立方没有情感,而人类有之;酷立方哪怕披上人皮,内心依然无有对社会生活的些许温情,而人类星球互通、人与非人相互联通的24世纪初,依然亟需保有“成为真实自己的机会”。《2312》被誉为科幻小说的拓疆之作,自2012年发表后斩获包括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正是因为其中不仅有对人类利用科技谋求一己私利的批判,更有对星际之间相互合作、互利共赢、追求正义、实现各星球和谐共存未来的展望。小说也提示人们,在一个科技似乎可以改变一切的时代,人们对自我身体、星球生态和生命的尊重,仍然是人与宇宙共存发展的必要前提。在宇宙中,地球只是“沧海一粟”,正如在地球上我们人类是渺小之辈一样。人类的足迹可以踏至星辰大海、上天入地,但无论身在何处、与谁相处,人之常情中的道德感应当永存。
在这些优秀的科幻小说中,科技滥用的背后,映射出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因果关系。若科技沦为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则无法造福生命。人类需要科技,但高科技的发展却要有伦理为最根本的参照,否则就可能会造成灾难性、毁灭性的后果。科技伦理和科幻小说经典中强调的人性与道德感,恰恰能够给当下投身科技事业、使用科技产品的人们带来启发。(张生珍)
来源:文汇报
标签:

03-18 14:53:54

03-18 14:51:07

03-18 14: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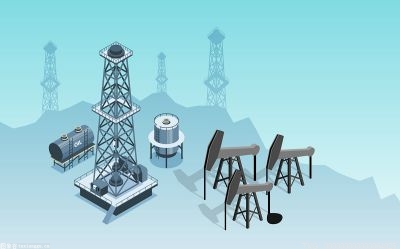
03-18 14:44:44

03-18 14:40:44

12-04 14:30:57

